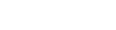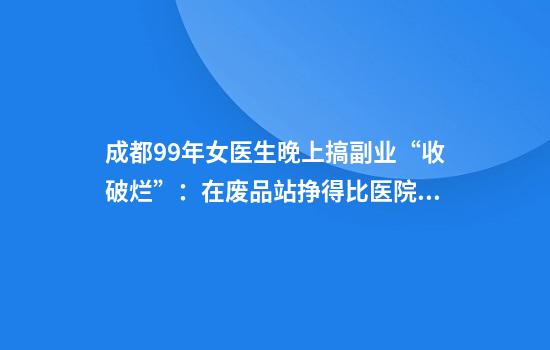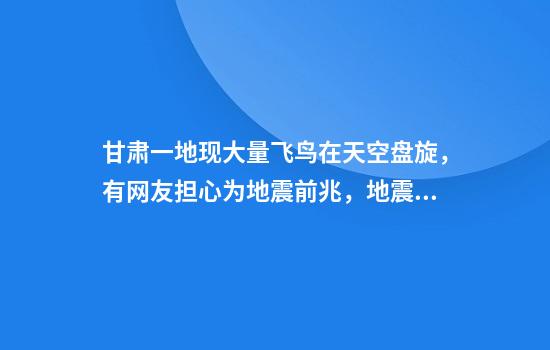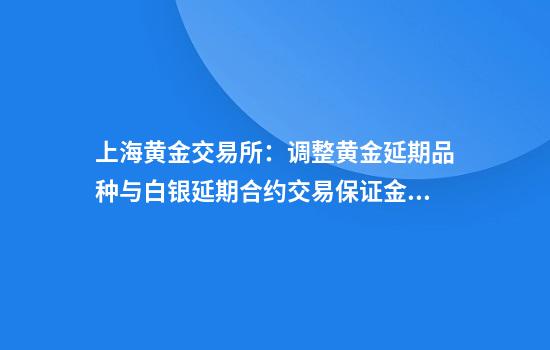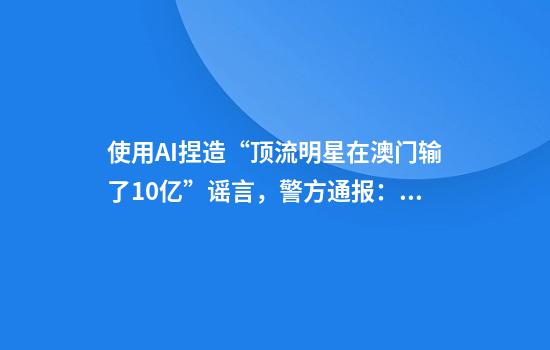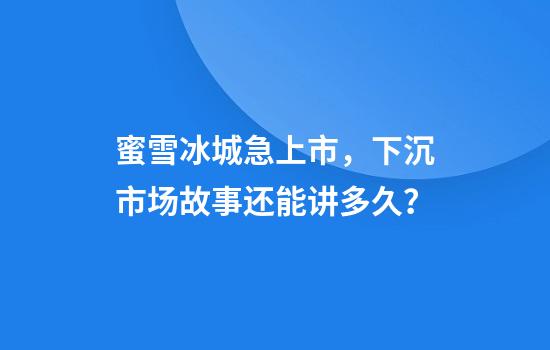在网贷平台只需几分钟的审核时间里,年轻人就能获得几千到上万元的 " 信用额度 ",而真正偿还这笔钱,往往需要数年,甚至拖垮整个生活。
他们是骑着电动车送餐的外卖员,是靠提成吃饭的销售,是想翻身的直播创业者——在高强度工作与碎片化收入之间,他们借钱只是为了 " 活得像个人 ",但当催收电话、逾期利息与系统性羞耻接踵而至,生活变成一场无法逃离的围猎。他们试图上岸,也有人选择逃离,更多的人困在沉默与孤立中。
这不仅是个体的困境,而是一个社会在信贷技术狂飙之后,留下的裂缝。我试图通过几个年轻人的故事,看清这套系统的运作逻辑,也重新理解,在 " 债务 " 之外,一个人还能如何保有尊严与出口。
不是不想还,是根本还不起
晚上 8 点,手机安静了下来。小刘习惯性地翻了下屏幕,今天一共来了 46 个电话和 70 条短信,大多来自他已经记不清的催收平台。陌生号码背后是类似的话术:" 您好,提醒您今日账单即将逾期,请于 23:00 前完成还款,否则将影响您的征信记录。" 短信末尾通常会加上一句," 为了您的信用,请及时处理。"
他将手机调成飞行模式,像是按下了一个暂停键,世界顿时安静下来。可那种安静,更像是神经上的真空。即使铃声停止,他也无法彻底放松。小刘知道,催收不会真的停下。明天一早,电话和短信又会开始,它们不会疲倦,不讲情面,也从不需要解释。
他坐在窗前,望着远处的高架桥,车流不断,白光流动。他的出租屋位于一栋老旧的筒子楼里,屋里只开了一盏桌灯,照亮了狭小的空间。桌上摊着一张外卖订单表,他今天跑了 37 单,收入不到两百块。这是他来北京的第 10 个月。最初,他以为靠勤奋可以换来稳定的生活。但现实证明,跑得越快,只是让他跌得更重。
小刘第一次借网贷,是在他来北京的第二周。那时他手机坏了,急需换新,身上只剩五百块。他刷到一个分期平台,只要身份证和手机号就能 " 极速到账 "。他没多想,点了确认。那一刻,他还没意识到,自己已经踏进了一个看不见的陷阱。
接下来的几个月里,他陆续在多个平台借钱:用一个平台还另一个,用工资补洞再制造新的洞。有时候只是为了凑房租,有时候只是为了吃一顿热饭。他清楚自己越来越难脱身,却也找不到退出的路径。" 总想着先撑过去这个月,下个月一定会好一点。" 他说," 可每次月初都比上个月更糟。"
每个平台的 APP 都像一个计时炸弹,红色的数字提醒他还有多少小时会 " 超期 ",会产生多少 " 违约金 "。有些平台的日利率高得惊人,一旦拖延一天,成本就翻倍。他也曾试图和客服沟通,分期还款、申请延期,但换来的只有机械的语音回复或者干脆的拒绝。" 平台没有情绪,它只看数字。"
在这种生活里,羞耻感是最先被摧毁的。他开始不接父母电话,不敢和老朋友联系,也不再在朋友圈发任何动态。他不想解释自己为什么连一百块都拿不出来。在外人眼里,他是个勤劳努力的年轻人,但在他心里,自己已经是一个信用破产、前路模糊的 " 失控者 "。
那天深夜,他梦到自己被无数手机追着跑,每一个铃声都像警报。他从梦中惊醒,身上全是汗。他不知道这个梦意味着什么,但他清楚一点:这不是噩梦,这是现实的一部分。
算法懂你,比你自己还早一步
小刘曾试图做一次完整的清算。他在手机里建了一个明细表格,列出所有欠款平台的名称、欠款金额、利率、逾期天数和催收频率。一共 14 个平台,有的是他自己下载的 App,有的则是第三方 " 智能推荐 " 时跳转的链接。他认真核对每一项,填了半个小时,最终还是关掉了表格。那个页面太像一张冰冷的体检报告,而每一个数据都是一颗正在计息的定时炸弹。
他已经记不清最早欠的是哪一家。起初只是三五百块,短期应急。但很快,那些平台就像嗅到血的鲨鱼一样,纷纷发来 " 授信邀请 "。有的短信开头写着:" 尊敬的优质用户 ";有的直接弹窗显示:" 恭喜您获得 6000 元额度,点击立即到账 "。利率几乎没有人细看,反正界面上写着 " 日息低至 0.03%",点进去却发现服务费、管理费、技术费层层叠加,真实利率高得令人瞠目。
" 钱太容易借了,几乎不需要思考。" 小刘说," 我有时候半夜点进去,不到三分钟就到账了。"
而催收,才是他真正开始感到恐惧的地方。
最初催收还算 " 文明 ",就是按时打电话、发提醒短信。但逾期超过五天后,平台就将他的 " 债务 " 转交给了外包催收公司。那些号码从全国各地打来,有些标注着 " 福建厦门 "、" 河南郑州 ",也有一些干脆显示为 " 骚扰电话 "。他试过接听,有人一开口就带着狠劲:" 你小子是不是不想还了?我们已经查到你家地址了。"" 不还没关系,我们找你单位领导聊聊。" 对方说话时带着一种玩弄的冷漠,那不是试图解决问题,而是一场彻底的信息博弈与情绪压制。
有一次,小刘在送单途中接到一个电话,对方直接叫出了他父亲的姓名和他老家的门牌号。" 我们已经发律师函了,下一步就上征信,诉讼。" 那天他险些撞到前方的隔离带。
更深层的恐惧并不来自于 " 还不上 ",而是 " 不知道该怎么办 "。借贷人一旦逾期,就迅速进入一个非理性的情绪深渊:愧疚、恐慌、自责、羞耻,还有无所适从。他们被催收员一步步引导去面对 " 最怕让谁知道 " 的人,比如父母、老板、女友。他们常常不得不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,卸载所有社交 App,把自己 " 从世界中摘除 ",以换取一点喘息。
" 不是我不想还。" 小刘反复说," 我只是想自己解决,不想别人看不起我。"
从网贷诞生的那一刻,它就带着一种 " 消费包容幻觉 "。平台宣传中强调 " 先享后付 "" 信用就是资本 ",许多年轻人第一次接触信贷并不是因为贫穷,而是因为平台给予的 " 资格感 "。比如在校大学生,在没有收入来源的情况下,也能获得数千元授信额度。平台不会质疑他们的还款能力,只要他们愿意点下 " 确认 " 按钮。
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金融平权,而是另一种门槛更低、代价更高的诱捕机制。
中国电子商会旗下消费服务保障平台消费保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,截至 2025 年 2 月 25 日,消费保累计收到网贷相关投诉超过 19 万件,累计涉诉金额超过 21 亿元。"2024 年消费保收到的累计投诉量高达 79025 件,同比 215.22%。" 消费保有关负责人曾公开表示,在网贷平台主要投诉问题中,暴力催收、乱收费、隐私泄露等三大问题占比约五成,其中暴力催收和乱收费的投诉分别占 20.64% 和 16.79%。利息问题、强制下款和提前还款及征信问题也是该行业的主要问题。
催收是一门生意,而不是一项服务。
大量的催收公司承接多个平台债务,以 " 佣金计价 ",即追到账多少,按比例提成。一些 " 激进话术 " 被包装成 " 心理攻势技巧 ",写进培训手册里。一位曾在催收行业工作两年的前员工表示:" 我们要做的,不是理解他们,而是让他们快速还钱,不管用什么方式。" 他承认,很多人并不真的 " 有能力还 ",但公司不会考虑这些,只关心数字是否到账。
他们中,有人上岸了,有人崩溃了。
在一些网贷自救互助群里,常能看到这样的留言:" 求问有没有能分期协商的平台?"" 刚刚接到电话,说我会被‘司法冻结’,是真的吗?"" 我真的不是老赖,我只是走不出去了。" 更多时候,这些群只是一个临时的情绪集散地,人们在其中倾诉、分享应对话术、转发 " 催收停息申请模板 ",仿佛在一场看不见的战役中寻找一丝集体的力量。
小刘也曾进过这样一个群。他看了一会儿,没发言就退了。不是因为不需要帮助,而是因为那些问题,他已经问过自己无数次。现在,他更愿意静静坐着,等那一天真正到来。
不只是欠钱,是无声的社会审判
小刘的经历并不罕见。当前,不少年轻人陷入网贷纠纷中。消费保数据显示,在网贷行业投诉用户中,男性占比 55.17%,女性占比 44.83%;在年龄分布上,90 后投诉占比最高,为 55.07%,80 后和 00 后占比分别为 29.77%、8.14%。
而在另一个城市,29 岁的琳琳正在吃力地整理她的 " 还款日历 "。她已经尝试 " 上岸 " 半年,每个月工资一到账,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记账 App,先把各个平台的最低还款额补上,然后再决定这个月还能不能交房租、买菜或出门。她是一家教育公司的课程顾问,底薪只有三千,收入主要靠业绩提成,但因为疫情后线下业务萎缩,公司连着几个月发不出奖金。
她第一次借网贷,是为了给自己买一部手机。她说," 当时同事们都用 iPhone,我用的是个旧国产机,打电话都断断续续。" 平台没有拒绝她,反而自动 " 授信一万 ",页面设计得像一个游戏奖励:" 恭喜您成为尊享用户!" 她觉得自己 " 也配得上点好东西 "。
接下来,是几次旅游、朋友聚会、买护肤品,几千块就这么花出去,后面就是补不上账的连环反应。
琳琳没有告诉家里,也没有告诉男友,直到有一天平台致电她公司前台。她在厕所里接听电话时,眼泪瞬间涌出来。" 那一刻不是因为怕,是羞耻。" 她说," 我一直以为自己可以独立处理这一切,可现实太快压下来。"
那次之后,她主动联系了各个平台,申请停息挂账、分期还款,很多都被拒绝,但也有几个愿意协商。她尝试过跑外卖,晚上七点下班就去站点报到,一直到凌晨,回家连衣服都顾不上换。她的膝盖在一个雨夜骑车摔倒后留下疤痕,但她坚持了三个月。终于在今年春节前,把欠款从原来的 4 万多压到了 2 万以内。
" 上岸不是一次胜利,是很多次放弃的反复选择。" 她说。她不后悔借钱买手机,但她现在不会再点开任何 " 来钱快 " 的链接。
和琳琳不同,23 岁的阿浩已经决定 " 逃离这个系统 "。
他是一个小镇青年,中专毕业后进过工厂、做过保安,也干过一段时间的直播带货。第一次借网贷是为了凑直播启动资金。他以为只要流量做起来,就能靠广告还债。但现实中他一个月也卖不了几单,没流量也没转化,只有不断追加的设备费和广告推广费。三个月后,他欠了六家平台的钱,总额超过 1.5 万。
他试过还,但根本填不完。平台利息有的高得离谱,虽然 2025 年新规明确网贷综合费率不得超过 24% 超过 24%,但平台玩起 " 数字游戏 ",将利息拆分为 " 基础利率 + 担保费 + 服务费 ",组合后突破 36%。他也意识到,自己 " 被当韭菜割了 "。
现在,阿浩不再接任何电话,也不工作了。他搬到广州城中村的一个合租房里,靠打零工和室友凑饭吃。他说:" 我不是不想还,我只是不想再被这个系统玩弄了 " 他计划离开城市,去云南或者西藏 " 断网生活 ",重新开始,他觉得反正已经逾期了等我后面赚了钱再慢慢一点一点来还吧。
" 这个国家有太多人像我了,信用爆了就像人被开除了户籍。" 阿浩苦笑着说。
这些年轻人里,有人硬撑着 " 走完账 ",有人选择从系统中 " 逃离 ",也有人陷入深度抑郁甚至轻生。
在知乎、豆瓣、小红书等平台,关键词 " 网贷 "、" 自救 "、" 崩溃 " 下聚集了大量匿名帖子,记录着无数夜晚的恐慌与自责。
" 债不是最可怕的,可怕的是那种‘我好像谁都不能说’的感觉。" 一位网友写道," 你以为你只是暂时困难,但平台不会给你时间。你以为是几千块的问题,到后来是你整个人都没了尊严。"
他们不是老赖,他们是跌入结构陷阱后试图挣扎的普通人。没有恶意,没有逃避责任的野心,他们只是太年轻,太快被世界的 " 金融逻辑 " 淹没了。
回到北京,小刘依然照常送着外卖。他开始关闭通知权限,把每个平台的 APP 都藏进文件夹最底部。现在,他不再做 " 全还清 " 的计划,而是先活下来,先一单单跑完今天。" 你问我有没有想过彻底还清?当然想过。" 他说," 但有时候,人活着也不只是为了还钱。"
债务背后,是一场社会的深层裂痕
在这个互联网极度发达的时代,借钱从来没有变得如此简单。而与此同时,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借钱,变得越来越复杂。
" 你为什么会欠债?" 是一个带着道德预设的问题,它在语义上已经暗示了 " 个人的失败 " 与 " 自作自受 " 的倾向。但如果我们放下对个体选择的轻易指责,转而去看这些债务背后的结构性诱导,我们就会发现,这场看似私人化的金融崩塌,其实是一种日常的、广泛发生的社会性困境。
从技术上看,网贷的 " 繁荣 " 与普及,是算法与风控系统的胜利。平台通过大数据建模、AI 风险画像,几秒钟内就可以决定一个用户能否放贷、放多少。表面上,这被包装成 " 普惠金融 ",是对传统银行门槛的补充。但实际中,这些技术更像一台精准测算人性弱点的机器——它知道你在哪个时间节点最可能点击 " 确认借款 ",也能判断你在什么样的语气攻击下最容易还款。
这个系统不需要了解你是否真的有收入,只要你愿意签署一连串默认协议,它就可以绕过一切信用背书,把钱送到你账户里。那一刻,个体的 " 理性判断 " 其实已经沦为工具变量,金融行为变成了平台的 " 操盘游戏 "。
更重要的是,这套系统是单向透明的:它看见你的一切,你却看不见它的深度。
我们从来不清楚,所谓的 " 服务费 " 是怎么算出来的,也不明白,利息和滞纳金在哪个维度开始急剧膨胀。每一次拖延,都不是一个具体的错,而是踩中一个已经预设好的惩罚机制。而这些机制,往往游走在监管之外,在 " 合法 " 与 " 灰色 " 之间取得商业最大化。
在国家层面,近年来监管部门已多次出台政策限制高利贷、取缔不合规网贷平台,推进 " 暴力催收 " 整治。2024 年 4 月 18 日起施行的《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》首次新增 " 消费者权益保护 " 的章节,明确要求消费金融公司不得采用暴力、威胁、恐吓、骚扰等不正当手段进行催收,不得对与债务无关的第三人进行催收。
2024 年 5 月 15 日,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的《互联网金融贷后催收业务指引》明确,金融机构和第三方催收机构应只向债务人催收,不应向联系人催收。在催收时间方面,晚 10 点至早 8 点禁止催收。以语音形式(含智能语音)进行告知式催收,每日合计不得超过 3 次。但真正渗透到底层生活中的网贷文化,却没有那么容易清除。一方面,正规银行难以覆盖的小微群体,依然只能依赖线上放贷作为短期应急手段;另一方面,消费主义和 " 即时满足 " 的心理趋势在年轻人群体中早已深入骨髓。
你很难要求一个月薪三千的人,完全抵御住一个 " 只需身份证即可获得 6000 元额度 " 的诱惑,尤其当这个诱惑出现在他刚发完工资、钱包空空、而他正在翻看朋友圈里别人刚买的新手机时。
从心理学视角看,债务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状态,更是一种社会状态。它剥夺的是人的 " 时间权 " ——也就是决定如何度过未来的权利。
一个背负债务的人,无法自由地规划人生。他们往往会陷入一种 " 当下压缩 " 状态:每一天都在为昨天的错误买单,每一个念头都要计算得失。他们的生活空间缩小了,他们的情感连接断裂了,他们的社会身份在 " 欠钱 " 这件事面前变得边缘和模糊。
债务也往往裹挟着羞耻。
在多数公共话语中,负债是一件 " 不光彩 " 的事,它被默认为是 " 无能 "" 懒惰 " 甚至 " 堕落 " 的结果。这种语境,使得陷入债务的人越来越沉默,不愿求助、不敢暴露,于是只能越陷越深。
但现实中,很多 " 负债者 " 其实极其努力。他们日复一日地工作,加班、接单、节食、压缩生活。他们不是不负责任的人,而是在某一个时间节点,被一种近乎系统性的力量推了一把。
这并不是在为一切借贷行为开脱,也不是否定个体在选择中应承担的责任。问题在于:在多大程度上,我们允许一种隐蔽的、不透明的机制,悄悄地将不堪与痛苦转嫁给个体?
而如果责任始终被归咎于最下层的那一群人,我们就无法真正看清这个社会系统中正在断裂的缝隙。
或许,有一天我们可以建立一种新的金融伦理。它不再是 " 诱导—放贷—惩罚 " 的三段式收割,而是一种兼顾风险与人的尊严的关系机制。在这样的机制里," 借钱 " 不再是一个羞耻的动作,而是一个被看见、被支持、被合理处理的过程。
回到开头的那个夜晚,小刘坐在出租屋的窗前,手机在桌上静静地亮着。他没有再去接那个电话,也没有再打开那个贷款 App。他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,车流穿梭,楼宇发光。这个城市依然喧嚣,他的债务没有减少,他的困境没有解决,但他感受到一种迟到的平静。
那不是 " 还完了 " 的轻松,而是 " 活下去 " 的微光。